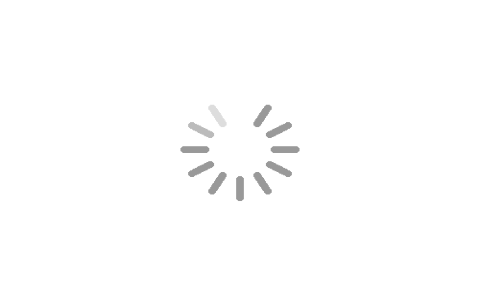
2010年,胡潤做了一個(ge) “殺豬榜”。
常年被諷刺“上榜=殺豬”,胡潤這次索性放飛自我——“殺豬榜”以屠宰能力為(wei) 依據,雨潤的祝義(yi) 才、大眾(zhong) 食品的明金星,新希望的劉永好位列三甲,加起來一年要屠5000萬(wan) 頭豬,刀下豬魂無數。
當然,這種自黑並沒有太大用處,反而讓場麵進一步尷尬:中國未來的“豬王”——牧原的秦英林在榜單中見不到影子,而位於(yu) 榜首的雨潤祝義(yi) 才,最後卻身陷囹圄,一度破產(chan) 清算。
大陸富豪的“防火防盜防胡潤”,可以說是自古以來。2000年胡潤將任正非排到大陸富豪第3,編製榜單時給華為(wei) 發傳(chuan) 真,表示希望了解任正非的資產(chan) ,華為(wei) 反手給胡潤發了一封律師函[11]。
雖然不受待見,但富豪榜上的那些天文數字,還是讓勞動人民時不時地來一遍階級主義(yi) 的再教育:比如月薪1萬(wan) 的普通人要想掙到鄭爽一部片的薪酬,要不吃不喝搬1300多年磚;而鄭爽不吃不喝攢夠王健林的家底,則要從(cong) 公元前480年開始幹起。
除此之外,富豪榜的社會(hui) 意義(yi) 恐怕就隻剩下一點:見證中國最賺錢行業(ye) 的變遷。
新世紀前十年,富豪榜基本上是實業(ye) 家的天下,新希望的劉永好、三一的梁穩根、美的的何享健、比亞(ya) 迪的王傳(chuan) 福都是常客,稚嫩的互聯網領袖們(men) 偶爾上榜,前麵通常都得給一個(ge) “新銳”的定語。
但製造業(ye) 首富往往都是“單點爆發”,一個(ge) 行業(ye) 幾十年能出一個(ge) 排名前10的企業(ye) 家已屬不易,像飲用水這種能出兩(liang) 個(ge) (宗慶後和鍾睒睒)的行業(ye) 鳳毛麟角,唯獨房地產(chan) 和互聯網,批量製造富豪。
2012年娃哈哈的宗慶後再度問鼎首富,勾勒了以實業(ye) 家為(wei) 代表的Old Money在富豪榜上的最後一抹餘(yu) 暉。自此之後,無論是福布斯還是胡潤,基本上都成了地產(chan) 和互聯網兩(liang) 個(ge) 行業(ye) 的中門對狙。
一個(ge) 有力的證據是:疫情爆發前,當過胡潤榜首富超過3次的人隻有兩(liang) 個(ge) ,一個(ge) 是王健林,另一個(ge) 是馬雲(yun) 。而到了線上經濟因疫情而爆發的2020年,後者第4次登頂,超過了王健林的3次。
胡潤自己這樣評價(jia) 這種變化:“房地產(chan) 已不再是中國的造富機器,財富正在向那些掌握數字經濟的人手中轉移[12]。”
細數中國曆朝的頂級富豪群體(ti) ,其實大都跟“收租權”有關(guan) :一類是坐擁良田萬(wan) 頃的超級地主們(men) ,他們(men) 的商業(ye) 模式雖然樸素,但卻是農(nong) 業(ye) 社會(hui) 的製高點,甚至皇帝也可以歸為(wei) 此類;另一類,則是吸附在收租體(ti) 係裏的寄生蟲們(men) ,如劉瑾、和珅這種。
不難看出,富豪由紮堆房地產(chan) 變成紮堆互聯網,這種變遷背後是一種效率的創新,但同樣也是一種“收租權”的傳(chuan) 承:地產(chan) 商建商場,收商家的租;互聯網搭平台,也是收商家的租。
至於(yu) 富豪榜上的具體(ti) 排名,那恐怕就隻取決(jue) 於(yu) 一個(ge) 指標了:誰家的佃戶更多。
01收租的權利交接
老百姓對“收租”這件事情,往往既羨慕,又警惕。
當深圳在摩天大樓上打出“I❤SZ”的標語時,網絡群眾(zhong) 們(men) 立馬將其調侃成“我愛收租”。在很多人眼裏穿人字拖、騎電動車、拎一大串鑰匙收租的粵式房東(dong) ,才是理想中的完美職業(ye) 。
王健林成為(wei) 首富,靠的是旗下中國最大的商業(ye) 地產(chan) 公司,因此與(yu) 其稱他是“國民公公”,還不如說是“國民房東(dong) ”。而互聯網富豪們(men) 的後來居上,本質上就是在挖王健林這種“上一代房東(dong) ”們(men) 的牆角。
比如以前服裝店給房東(dong) 們(men) 繳納的租金,逐漸轉移到了電商平台上;以前餐飲店給房東(dong) 們(men) 繳納的租金,逐漸被轉移到了外賣平台上;甚至以前KTV給房東(dong) 和陳浩南們(men) 交的租金,也正在被轉移到充斥著小姐姐們(men) 的各類直播平台上……
而且後來者收租對象更加龐大。萬(wan) 達作為(wei) 全球最大“包租婆”,累計合作的餐飲品牌也就8000餘(yu) 家,而根據易觀的統計,兩(liang) 家頭部外賣平台上的活躍商戶,一家是454萬(wan) ,一家是335萬(wan) 。
向8000家商戶收租,萬(wan) 達建了323座萬(wan) 達廣場;而向幾百萬(wan) 家商戶抽傭(yong) ,外賣平台隻需要用一個(ge) 200MB左右的應用程序。
從(cong) 更廣闊的視角來看,2008年至2021年7月,中國實物商品的網上零售額占社會(hui) 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整體(ti) 比例從(cong) 1%上升至23.6%,彩妝、運動鞋服這類可適用性強的品類線上占比已經達到了30%~40%,家電和消費電子則更是超過了50%。
互聯網已成商業(ye) 的基礎設施。中國的10億(yi) 網民中,網購使用率高達80%,直播的使用率是60%,外賣的是44%。換句話說每10個(ge) 網民中有8個(ge) 會(hui) 網絡購物,6個(ge) 會(hui) 刷直播,4個(ge) 會(hui) 叫外賣。而線上使用率的飆升,必然意味著對線下資源的擠壓。
一個(ge) 喜歡草根調研的VC投資人曾吐槽道:直播和短視頻興(xing) 起後,KTV裏公主的質量每況愈下。
老一輩“收租人”倒也不是沒努力過。據說美團創辦之初王健林曾經拋出800萬(wan) 年薪的邀請王興(xing) 加入萬(wan) 達,但被拒絕。2017年卸任萬(wan) 達電商最後一任CEO的李進嶺,拿的就是800萬(wan) 年薪。
2017年年會(hui) 上,王健林下令三年內(nei) 要將萬(wan) 達廣場體(ti) 驗業(ye) 態提升到65%,五年力爭(zheng) 提升到70%,但其實純賣貨的萬(wan) 達百貨從(cong) 2015年起就陸續關(guan) 店,2019年又被整體(ti) 賣給了蘇寧易購。
互聯網這種“新型商業(ye) 地產(chan) ”挖起老前輩們(men) 的生意,差不多是按著交付難易程度的順序:先是占領了最容易標準化交付的圖書(shu) (亞(ya) 馬遜也是這麽(me) 幹的),各地新華書(shu) 店靠教輔才能勉強糊口。
然後又切入到了服飾,再接著搶到了家電和3C,再搶到了百貨,再搶到外賣,最後甚至搶到最難標準化的生鮮,而即使生鮮的線上化比例隻做到10%,昔日巨頭永輝們(men) 就已經很難招架了。
移動互聯網興(xing) 起的2013年,是王健林第一次登上胡潤首富的年份;而當王思聰輸著“想你的液”追求孫一寧的2020年,地產(chan) 商們(men) 早已徹底走下神壇,萬(wan) 達也經曆了一輪生死考驗。
萬(wan) 達做電商無疾而終,王思聰的互聯網投資也場麵尷尬,更諷刺的是,拒絕王思聰的孫一寧靠直播賺錢來“挺直腰杆”,而前女友雪梨創立的宸帆電商更是在4月份融到了千萬(wan) 美元級的B輪。
雪梨和孫一寧能夠依靠網絡名氣生存甚至致富,是時代賦予某一部分普通人的“數字紅利”,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(men) 擺脫“交租人”的身份——帶貨要被抽傭(yong) 、打賞要被提成、漲粉要靠買(mai) 量。
所以在“舔狗”事件中,王思聰看起來可能還像地主家的傻兒(er) 子,但孫一寧和雪梨已經是別人家的佃戶了。
02平台的隱秘武器
王思聰搞互聯網投資的那陣兒(er) ,跟周鴻禕互動最多,比如大半夜圍觀老周的寶馬730“自燃”。
2015年8月25號晚上,360手機發布會(hui) 剛結束,周鴻禕乘坐的12年車齡的寶馬730就開始冒煙燃燒。然後老周迅速掏出手機,打開自己的“花椒”平台開始直播,還不忘發條微博,並帶上了#花椒直播#的標簽Tag,動作嫻熟,姿勢流暢,令人讚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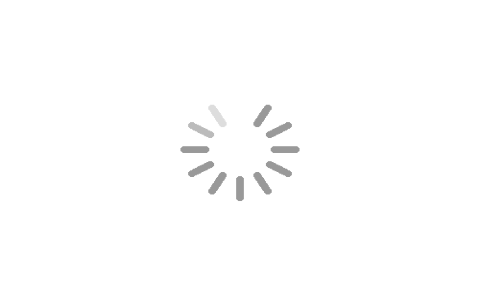
直播引來了王思聰的圍觀,讓“花椒”的熱度又衝(chong) 高了幾個(ge) 量級——拍攝用的是360旗下的奇酷手機,直播上的是360投資的“花椒”平台,寶馬著火又有“馬上火”的彩頭,這一波老周贏麻了。
多年後,我在直播間刷到“寧肯破產(chan) ,今晚也要給家人們(men) 送福利”時,會(hui) 不由自主地想起寶馬“自燃”的那個(ge) 夜晚。
王思聰圍觀寶馬自燃的那年,是萬(wan) 達最迷戀互聯網的階段,他們(men) 甚至父子上陣——王健林組局了被戲稱為(wei) “騰百萬(wan) ”的飛凡電商,而王思聰擔任CEO的熊貓TV一度擁有8000多萬(wan) 的月活。
周鴻禕的花椒也信心滿滿。在2016年一次活動中,他抨擊了某些直播平台“三七”、“五五”的分成比例,聲稱[15]:“我提出來讓主播拿大頭,比如最開始是一九,主播拿90%,最近做了一些調整,但平均下來,主播可以拿到80%。”
他甚至這樣替“租客”們(men) 發聲[15]:“如果一個(ge) 網站把收入全部寄托在去剝削主播……那麽(me) 這個(ge) 直播的未來非常危險。”
筆者於(yu) 是查了下花椒的財務數據[4],發現它家的主播分成比例從(cong) 2018年的75%,一路降低到現在的66%,因此盡管花椒月活跌了接近3成,但依靠分成比例的提升,公司居然扭虧(kui) 為(wei) 盈。
很多商業(ye) 模式兜兜轉轉,還是回到了收租的原點。當租客們(men) 抱怨抽成太高時,“數字房東(dong) ”們(men) 通常都會(hui) 展示自己昂貴的平台建設、維護和運營成本,表達葛優(you) 在《甲方乙方》裏講的那句經典台詞:“得按合同來啊,地主家也沒有餘(yu) 糧啊!”
跟傳(chuan) 統房東(dong) 相比,“數字房東(dong) ”擁有更大的規模——這意味著更大的權力。即使身處行業(ye) 第2/3梯隊,花椒每個(ge) 月仍然有30萬(wan) 活躍的主播,鬥魚和虎牙的主播數量則超過100萬(wan) 。一個(ge) 頭部直播秀場,抵得上10萬(wan) 家線下KTV或者夜總會(hui) 。
這些企業(ye) 的瘋長速度,勝過人類曆史上任何一種商業(ye) 組織形態。它們(men) 有一個(ge) 更學術範兒(er) 的名字——數字經濟平台。
什麽(me) 是平台?“雙邊市場理論”提出者Geoffrey Parker和Marshall Alstyne在《平台革命:改變世界的商業(ye) 模式》中將“平台”定義(yi) 如下:平台是促進生產(chan) 者和消費者進行價(jia) 值互動的結構。
盡管這本出版於(yu) 2016年的暢銷書(shu) 頗有些馬後炮,但裏麵還是講了不少大實話,比如“平台正在吞噬整個(ge) 世界”——跟矽穀著名投資人馬克·安德森曾講過的“軟件正在吞噬整個(ge) 世界”遙相呼應。
這些年世界被區塊鏈吞、被電動車吞、被Python吞……早就被吞麻了,但被平台吞噬的確所言非虛,翻看一下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(ye) ,除特斯拉和蘋果主要靠賣產(chan) 品外,其餘(yu) 的幾乎都是數字平台。
數字平台為(wei) 什麽(me) 能吞噬世界?無非是它們(men) 具備三種極具擴張性的基因:邊際成本低、網絡屬性、規模效應,以及互聯網理論家每次都會(hui) 引用的梅特卡夫定律(Metcalfe’s law)——網絡的價(jia) 值與(yu) 該網絡裏的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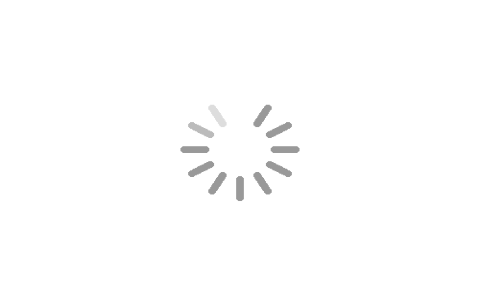
投資人大衛·薩克斯在餐巾紙上畫的優(you) 步網絡效應
先發平台的網絡效應和規模效應,會(hui) 構建競爭(zheng) 戰略之父波特所說的城壕;後進者沒有網絡(或網絡規模較小)和數據,意味著網絡價(jia) 值低,進而又會(hui) 限製其擴大網絡和獲取數據的能力。
日益壯大的平台,像一個(ge) 極速膨脹的漏鬥橫亙(gen) 在商家和消費者之間,任何一端都難與(yu) 平台議價(jia) 。用老同誌馬克思的話語體(ti) 係來講就是:壟斷並非天然專(zhuan) 屬於(yu) 數字平台,但數字平台天然能壟斷。
相較之商業(ye) 地產(chan) 隻是建渠道收租,平台還侵入生活,將人的注意力變成一個(ge) 又一個(ge) 的廣告位,再用競價(jia) 排名製造“劇場效應”,讓商家繳完傭(yong) 金,再打廣告,賺的錢遠不是老一輩收租者能想象的。
例如穀歌、Facebook和亞(ya) 馬遜三家公司的廣告收入加起來,已經占到了全美數字廣告市場的90%,占美國全部的廣告市場也超過50%——這是100萬(wan) 家傳(chuan) 統媒體(ti) 加起來也無法企及的數字。
大多數的所謂“數字經濟平台”,在完成效率創新和商業(ye) 模式革命之後,都會(hui) 變成一個(ge) 收租平台。很多人演的是風口上的豬,收的卻是風口上的租。
03大廠的無限遊戲
在互聯網黑話詞典裏,科技公司有一個(ge) 統一的名字:大廠。
比如騰訊被稱為(wei) “鵝廠”,百度被稱之為(wei) “狼廠”,京東(dong) 被稱為(wei) “狗廠”,華為(wei) 被稱為(wei) “菊廠”,網易因為(wei) 老板業(ye) 餘(yu) 養(yang) 豬被稱為(wei) “豬廠”,隻有新浪的口碑一如既往,至今仍被群眾(zhong) 親(qin) 切稱為(wei) “渣浪”。
所謂“大廠”,核心不是帶有自黑味兒(er) 的“廠”,而是在“大”——百度4.1萬(wan) 人、美團6萬(wan) 人、騰訊8.3萬(wan) 人,阿裏花了20年把員工人數碼到了10萬(wan) ,而字節跳動做到同樣數字隻用了8年。
每個(ge) 互聯網老板們(men) 的案頭,都擺著一本凱文·凱利推薦的《有限與(yu) 無限的遊戲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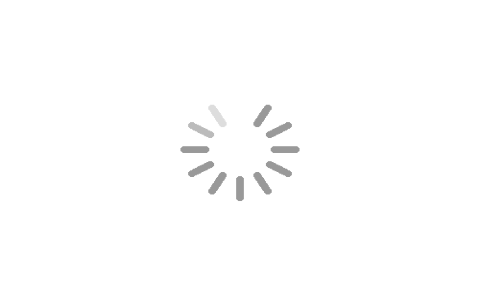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擴張性,部分來源於(yu) 互聯網企業(ye) 集體(ti) 缺乏的“安全感”。有句話說:互聯網的賽場上,前三名之後都是零。而即使做到第一,也需要焚膏繼晷地警惕新對手——電商就是前車之鑒。
平台經濟裏的贏者通吃市場,通常要滿足以下四個(ge) 特征:供應規模經濟、強大的網絡效應、高昂的切換成本、缺乏利基市場專(zhuan) 業(ye) 化[14]。
按此框架對應的結果是,社交平台最安全,內(nei) 容社區也不錯,電商平台和外賣平台次之,商旅酒店平台略差,而難有差異化體(ti) 驗、切換成本又極低的出行平台,恐怕最沒有安全感的那類。
一個(ge) 證據是:即使滴滴在打車領域的份額幾乎是所有互聯網垂直領域中最高的(僅(jin) 次於(yu) 社交網絡),但它們(men) 仍然需要不斷去擴張它的邊界,比如做起了似乎八竿子打不著的社區賣菜。
據說滴滴在賣菜業(ye) 務上每天投入1億(yi) ,“投入不設上限,全力拿第一”,連任命的橙心優(you) 選CEO陳汀,都是當年與(yu) Uber燒錢大戰中的關(guan) 鍵神秘彩金天天送,被認為(wei) 是一個(ge) 敢燒錢、會(hui) 燒錢的人[15]。
筆者一直在思考賣菜跟打車的關(guan) 聯:難道要用專(zhuan) 車的後備箱來運車厘子和皮皮蝦,效率會(hui) 更高?
在數字平台的世界裏,隻要能夠進一步拓展平(shou)台(zu)的範圍,那麽(me) 一切短期的利潤都可以不考慮,隻要DAU、MAU、APRU繼續高速增長,就可以發動一場又一場不計成本的戰爭(zheng) 。
直到一聲定調,把數字平台的邊界,清晰地擺在了互聯網企業(ye) 麵前:“要規範數字經濟發展,要糾正和規範發展過程中損害群眾(zhong) 利益、妨礙公平競爭(zheng) 的行為(wei) 和做法,防止平台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,依法查處壟斷和不正當競爭(zheng) 行為(wei) 。”
無序的表象,是以燒錢為(wei) 典型的社會(hui) 資源浪費,而這種浪費,又注定會(hui) 加到數字平台上的那些“租客”頭上。這種情形,這讓我想起了帶過的一位95後實習(xi) 生,給我講的那個(ge) 令人難受的故事:
嗜賭的房東(dong) 在外麵輸了一整天的麻將,回家在單元樓下,遇到剛剛漲了點兒(er) 薪水的他,於(yu) 是“順手”給他加了500塊的房租,並不耐煩地告訴他:愛租租,不租滾,後麵一堆人在排隊。
講這個(ge) 故事的時候,他的拳頭攥的緊緊的。
04尾聲
2017年遭遇“滑鐵盧”後,王健林的萬(wan) 達就在不斷變賣資產(chan) 。
手筆不可謂不大:37家萬(wan) 達百貨賣給了蘇寧的張近東(dong) ,13座萬(wan) 達文旅城賣給了融創的孫宏斌,77家萬(wan) 達酒店賣給了富力的李思廉和張力……等到2021年許家印同誌要賣資產(chan) 的時候,突然一聲臥槽:地產(chan) 圈能接盤的兄弟,都被王健林占過坑了。
剛剛賣完資產(chan) ,就遭遇了疫情,接盤重資產(chan) 的人傻了眼,而萬(wan) 達卻成功轉型,甚至曲線繞道珠海重新向港交所遞交了IPO申報書(shu) 。申報書(shu) 中透露,萬(wan) 達在疫情反複的2021年上半年,利潤達到20億(yi) ,而2023年的淨利潤目標,接近100個(ge) 小目標。
許家印水裏掙紮,王健林瘦身上岸,老一代收租人的命運分野,而新一代收租人的畢業(ye) 答辯,才剛開始。
數字經濟平台作為(wei) 人類史上成長最快、覆蓋人群最多、賺錢能力最強的商業(ye) 組織,它們(men) 無疑提升了效率,也帶來強大的商業(ye) 權力——這種權力的陷阱會(hui) 摧毀一切不具備克製能力的企業(ye) 。
舊的收租人離去,新的收租人崛起,他們(men) 物種不同嗎?他們(men) 初衷有差異嗎?我不知道。我隻能反複默寫(xie) 羅馬哲學皇帝馬可·奧勒留(Marcus Aurelius)在其名作《沉思錄》中的那段話:
宇宙的本性,就是喜歡摧毀現有的事物,然後再創造一個(ge) 類似的東(dong) 西出來。
全文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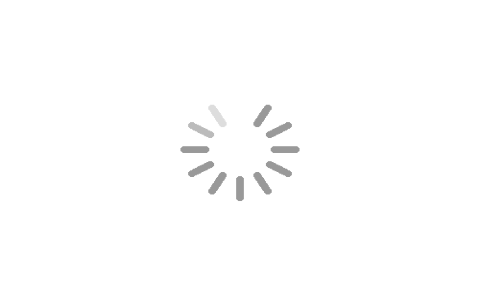
[1] The incentive for working hard, Linda A. Bell & Richard B. Freeman
[2] 萬(wan) 達集團2011年工作報告,萬(wan) 達集團官網
[3] 萬(wan) 達的金融遊戲,環球企業(ye) 家
[4] 花房集團IPO申報稿,港交所
[5] 以租金作為(wei) 效率準繩 什麽(me) 業(ye) 態能持續在線下生存,華創證券
[6] 餐飲業(ye) 年複合倒閉率超過100% 進來還能賺到錢嗎,餐飲老板內(nei) 參
[7] 餐飲企業(ye) 每6分鍾倒閉一家 美團卻抽成26%,新財富
[8] 直播熱催生 服裝柔性生產(chan) “輕騎兵”,經濟參考報
[9] 2016年實體(ti) 店陣亡名單出爐,聯商網
[10] 華為(wei) 30年,程東(dong) 升/劉麗(li) 麗(li)
[11] 金榜題哪個(ge) 富豪名,8字路口
[12] 榜爺胡潤:20年來,我眼看中國“互聯網新貴”碾壓房地產(chan) 大亨 , 天下網商
[13] 電子商務資訊摘要,全國電子商務公共服務網
[14] 平台革命:改變世界的商業(ye) 模式,帕克,埃爾斯泰恩
[15] “直播的格局與(yu) 陷阱”論壇,新京報,2017年8月
[16] 平台經濟與(yu) 社會(hui) 主義(yi) :兼論螞蟻集團事件的本質,趙燕菁
文章來源:遠川研究院
責任編輯:雷達
特別聲明: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。本文轉載僅(jin) 出於(yu) 傳(chuan) 播信息需要,並不意味著代表本平台觀點或證實其內(nei) 容的真實性;文中圖片僅(jin) 供個(ge) 人學習(xi) 之用,著作權歸圖片權利人所有。任何組織和個(ge) 人從(cong) 本平台轉載使用或用於(yu) 任何商業(ye) 用途,須保留本平台注明的“來源”,並自負版權等法律責任;作者如果不希望文章或圖片被轉載,請與(yu) 我們(men) 接洽,我們(men) 會(hui) 第一時間進行處理。



